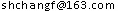- ■ 政府让开发商合理合法储备土地
- 发布日期:
- 2009-09-01
- 文章来源:
- 高端财经
- 文章编辑:
- 上海厂房网
-
“捂”这个词自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商品房供给的市场化早在十多年前就消失了,如今又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媒体的头版之中,并且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关键词了,而这个词的出现一定是伴随着市场化条件的不充分所造成的紧缺。
改革之前的商品供给是短缺的,是计划性分配与票证制的,因此捂或说囤积、储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能省则省的节约排在首位,省吃俭用成为习惯,人们会存粮票、存工业券、捂猪油、捂白菜、捂肥皂,不管是吃的用的能捂则捂。生存的需要让人们不得不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
家庭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毛主席引用的古语“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俨然成为了重要的国策。正是这种对未来短缺的恐惧培养出了建国之后至改革之初的无数代人。
改革之后一次次闯关的成功让80后、90后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新中国的前四十年都是在这种捂的文化之中渡过的。因此一有风吹草动自然就勾起了他们的回忆,自觉与不自觉的他们都会重新拿起捂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未来。
为什么中国实行土地的“招拍挂”制度之前,市场上从来就没听说过有捂地、捂盘的现象。因为人们没有土地被严格控制的预期,而2003年双紧的闸门一关,8.31大限的重锤落地,让市场恍然大悟,土地变成了垄断形成的高价面粉。“死守十八亿亩红线”的十二道金牌和耕地已逼近十八亿亩红线的资源紧缺矛盾的暴露,让中国从上到下传播着一种未来无粮的恐慌。国务院在为“十八亿亩红线”发愁、地方政府在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用地矛盾发愁、财政在指望土地收入的支撑,且不说地方政府有多少的违规违法占地行为(远远大于开发商的合法行为)至少土地从2003—2006年连续四年的供给下降让开发商加重了危机感,让全世界加重了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严重不足的危机感,也才有了开发商不得不存粮等待过冬的准备。都说是因为投资者们过多的看重于上市公司的土地储备、过高的对土地给以估值,才让开发商在上市之前大量的储备土地,才造成了土地的天价和疯抢。但投资者为什么会过多的看重中国开发公司的土地储备呢?为什么对除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之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是用土地的储备量来作为估值的依据呢?原因很简单,除这些地方之外,世界各国都没有这种土地的供给制度,都没有这种稀缺性与招拍挂的特殊公地方式,尤其是没有中国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垄断的土地制度,自然也就没有对土地资源短缺的恐慌,那又何来的这种估值预期呢?
如果境内外的投资者都有这种预期,都认为中国的土地是个稀缺资源,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土地供给根本就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又如何让开发商会相信政府会有充足的土地供给呢?
除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企业之外,有哪个开发企业能不保留合理的土地储备与库存呢?这个合理性建立在市场的变化上,或者说供求的关系上。
一个流水作业的企业,至少会保有不少于三至四个生产周期的项目储备,至少让做前期工作的人员有活干,让设计管理的人员有活干,让施工管理的人员有活干,让采购的人员有活干,让销售的人员有活干。如果中间项目无法衔接上,那么管理团队不久散了吗?一个土地到具体施工条件的周期大约要9各月至18个月或者更长。
如果是规模较是中等的公司至少就要有双循环的项目条件,这样劳动力的组织成本才会降低,效率才会提高。大型企业则这种土地的储备就要更多了。
而一个项目的大小不同,则要从总规模上判断了。如一个企业年开复工的面积为500万平方米,销售为300—400万平方米,那么这个企业的双或三循环的储备至少要2000—3000万平方米(每个城市中的循环是叠加的倍数关系)。
当市场好时,这个储备量和开复工量就会扩大,反之则缩小,这大约就是经济学上的生产弹性系数了。而这个合理的储备量难道是捂盘吗?或者只是弹性系数的伸张而已。如果没有2008年和2009年上半年的紧缩,也许今天的土地储备早就严重不足了。正是因为在紧缩之后去统计,于是库存量略大的现象出现也是非常正常的。
是谁在让开发商合理合法的储备土地呢?
北辰长沙的用地92亿元,约5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请问长沙一年的商品房销售为多少,这个项目一年能开工多少、销售多少,要用几年完成,会有多少土地晒太阳?且不论市政配套的条件与能力,一年50万平方米的开复工也要十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至少50%以上的土地会存五年以上。为什么政府不将土地缩小、划开了去拍卖呢?
整体与整体规划的好处,有统一开发的好处,原因在于政府无能力做个好的符合市场要求的规划,也就力争先把钱拿到手,任由开发商代政府干活了。
迪拜也有数百万平方米同时开发的项目,但用地是规划好了的按楼座来卖的。每个楼座都有明确的用途、详规、开竣工时间的要求,27个国家同时开发建设也会前后差不多的周期内竣工,这才是市场化的操作。自然也就不会有捂地的问题了。但前期的准备中也许这个土地捂了十年也不止。这无非是前期准备的周期计算在谁头上的问题。
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教授告诉我们丹佛旧机场的改造规划用了七年,建设只用了六年。正是因为前期的准备时间充足,才会有不用十年、二十年后就不得不拆除的优秀建筑群,才会不给城市留下遗憾。
没有详细的规划与论证、没有充分的设计周期,又怎么会有好的建筑呢。
开发商拿到土地要调研市场、研究规划、申报审批,谁知道审批的周期有多长。政府任何的调整政策和规划都会让设计周期成倍增长。
90平方米70%的政策出台之后,大量的设计不得不推翻重来,土地自然要晒太阳。北京因奥运、六十年大庆、两会等各种原因,规划的审批长达两年以上的不在少数,这岂是开发商捂盘。
许多用地是毛地出让的,这些毛地中的拆迁问题,连法院都打退堂鼓,又有谁来保护开发商和投资者的利益呢。
危机时,大量的地方政府出台了缓交土地出让金的政策用以救市,那么这些未交齐土地出让金的用地,政府会提前发给土地证并进行后续的工作于审批吗?那么这些土地又如何不晒太阳呢?救市救人救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又查来查去的,讲责任推给开发商。
市场狂跌时,又有谁会大量的生产呢?请问大量囤积的铁矿石会消化吗?能反过来说是钢厂在捂铁矿石吗?
中国会储备石油、储备粮食、储备猪肉以调节市场,那么生产者就不能储备原料以调节市场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几千年来也未消失过。如今又更明目张胆的有理、有力、有强制了。
如果一个国家为了民生可以用储备来调节价格,企业为什么不能用储备来应付危机、规避风险与市场变化呢?国家为了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可以联合谈判,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市场秩序。开发商是否能为了土地价格而与政府谈判呢?难道只有钢材关系国家利益与民生,而住房不关系到民生吗?
没有开发商购买了天价地是为了亏本的,这与铁矿石价格谈判是一个道理,但市场的变化也许让天价地会亏损,晒太阳而等市场的转化又有何罪呢?只要不违背法律所规定的时限,为什么不能自我根据市场调节呢?当市场出现危机时生产要亏本,又有哪个行业不是用减产来调节价格呢?危机时又有哪个政府不出现政策改变合同或规定而救市呢?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出台救市政策不正是同心协力救市吗?
有人说天价地是政府谋利动机而造成的。但对公民而言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都属于“子不教父之过”,而无法推卸责任。假如没有财权与事权的差距,地方政府又何来的要拍个“天价”地以增加收入呢?
评论“捂”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中国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当开发商购买了七十年使用权的土地之后,如何使用与收益的财产权利已不再归政府或其他非财产权利人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无权指责财产权利人的使用方式和时间。如果有法律约定则应依法办理,如果有合同约定则应按合同办理,如果合同对有延期的违约责任则按违约责任办理,而不是按社会的舆论倾向办理。
法律约定了开发商的时限,但如果拿到土地的开发商没有违法,但延误了开发周期,那么接盘或重组的企业也许根本无法按法律规定的(或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工,是否也是违法或违约呢,是否应在重组土地资源之后重新计算时间和周期呢。仅以政府的土地出让时间计算是否捂地,那么许多的烂尾地和烂尾楼就无法重组了。
好像党的文件中早就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矛盾”,那么如何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适应于经济规律与周期就比社会舆论的非理性指责更为重要了。
2008年的经济下滑和房地产的市场恶化,让所有的新开工都处于下降和停滞状态,大量已开工的项目就停在了半截。2009年的上半年虽然销售转好,但开工量同比仍是负增长。市场的前景尚不确定、信心尚未恢复、宏观经济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短期改革效应不断削弱、政策回调的预期不断加大、长期政策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政策前景不明朗。虽然在个别城市中出现了土地的少数天价,但全国的土地购置量仍为负增长,如何让开发商可以放心的加大投入并增加开工。也许还在准备的阶段,至少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并没有完全的缓解,新增投资的增速不可能在一、二个月内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有些土地还会继续晒太阳。由于融资能力和资本实力的不同,因此土地价格的分配也极不平衡。贫富差别不仅表现在居民的收入之间,也同样表现在企业之间,而政府大片土地的出让无疑会减少中小企业生存的机会,并给了大企业土地储备的合理与合法的掩护。土地的私有化可以让美国的开发商以一幢或两幢的房子进行改造与开发,但中国则以数千亩或数万平方公里的方式供地,这些土地又怎么有可能不晒太阳呢?
解放前蒋介石曾下令屯粮者杀,但并未对非粮食经营者的企业、单位屯粮者杀。开发商不是土地的经营者,只是土地的消费者,土地就像铁矿石、煤炭、大豆、棉花一样,不过是下一个商品的生产原料。当国际大豆的价格让国内的大豆储量无法顺价销售时,就只好在粮库中晒太阳了。土地难道不是如此吗?
当讨论市场中的经济运行问题时,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就会忘记了法律、忘记了财产权利、忘记了经济规律、忘记了企业公民的尊严。也许是计划经济沉淀下来的传统,让管理者与社会常常忘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与权利。民意不能变成了民粹,站在法律的对立面成为破坏改革三十年成果的绊脚石。
- 标签:
- 上一篇:
- 成交量"低迷"背后 楼市或起商业地产抄底热
- 下一篇:
- 地价2年涨6倍,调控组合拳已刻不容缓
-
■ 相似信息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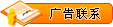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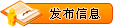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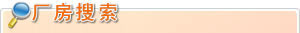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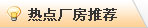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联系QQ:
联系QQ: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